
在這次去馬德里之前,我先經(jīng)過了巴黎和巴塞羅那。競(jìng)技
在巴黎街頭的懂球幾乎每一處游客商店里,都擺著至少一個(gè)柜子的夜話巴黎圣日耳曼周邊,甚至有不少店鋪的馬德遮雨棚上都有兩個(gè)大大的PSG隊(duì)徽;而在巴塞羅那,機(jī)場(chǎng)落地的競(jìng)技第一時(shí)間就能在航站樓里看到巴薩的官方商店,大街小巷和每一處知名地標(biāo)你都能看到很多件亞馬爾球衣。懂球
這兩座城市在足球上有一些共同特點(diǎn):在巴塞羅那幾乎看不到任何西班牙人俱樂部的夜話元素,在巴黎也完全沒有巴黎FC。馬德贏家通吃,競(jìng)技這對(duì)于很多擁有壓倒性榮譽(yù)優(yōu)勢(shì)豪門的懂球城市來說,似乎是夜話足球市場(chǎng)的一般規(guī)律。

但馬德里有所不同。
從某個(gè)角度來說,競(jìng)技皇馬在世界足球史上的懂球地位更甚,也有著更加深厚的“官方”背景,甚至曾一度被國家機(jī)器作為標(biāo)志球隊(duì)用于足球的宣傳敘事。
這光是從主場(chǎng)的位置就能看出不同:伯納烏的位置在馬德里的富人區(qū)查馬丁區(qū),甚至當(dāng)?shù)厝藭?huì)將這片馬德里房價(jià)最貴的商業(yè)區(qū)稱呼為“伯納烏區(qū)”。而馬競(jìng)的老主場(chǎng)卡爾德隆球場(chǎng)則是在西南的曼薩納雷斯河邊,著名的看臺(tái)下穿M30公路奇景,也正是這座球場(chǎng)所處位置的證明。甚至,馬競(jìng)的新主場(chǎng)大都會(huì)球場(chǎng)位于更遠(yuǎn)的馬德里東郊,從市區(qū)駕車過去還要經(jīng)過一段高速公路。

然而,在馬德里的足球版圖上,皇馬從未獨(dú)占鰲頭。馬競(jìng)憑借著自己獨(dú)特的魅力,始終占據(jù)著很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這與倫敦、米蘭和伊斯坦布爾的情況又有一些不同:阿森納和切爾西在國內(nèi)和洲際賽事中各擅勝場(chǎng),米蘭兩隊(duì)的頂級(jí)聯(lián)賽冠軍次數(shù)僅差1次,伊斯坦布爾則是三支球隊(duì)分庭抗禮壟斷國內(nèi)聯(lián)賽。而馬競(jìng)和皇馬相比,在頂級(jí)聯(lián)賽的奪冠次數(shù)上相差三倍之多,洲際賽事榮譽(yù)方面皇馬更是處于絕對(duì)領(lǐng)先地位。
但馬競(jìng)依舊能做到。

當(dāng)我深夜穿著馬競(jìng)球衣走在馬德里街上或是坐上出租車的時(shí)候,騎著車的年輕人和年長的出租車司機(jī)依舊會(huì)朝我喊Aúpa Atleti。這是馬競(jìng)的生存之道,也是馬德里的競(jìng)技之道。
馬競(jìng)的起源故事就很特別。
在20世紀(jì)初,現(xiàn)代足球剛剛開始從不列顛走向世界的過程中,馬競(jìng)的起源要通過二度關(guān)系才與英國產(chǎn)生了聯(lián)結(jié):來自巴斯克的留英學(xué)生返回西班牙后成立了畢爾巴鄂競(jìng)技俱樂部,而三名住在馬德里的巴斯克學(xué)生則成立了競(jìng)技的馬德里分部,也就是最初的馬德里競(jìng)技。
這一份聯(lián)結(jié)甚至也體現(xiàn)在了球衣上:1903年,愛爾蘭裔的畢爾巴鄂競(jìng)技俱樂部成員胡安·莫澤給俱樂部捐贈(zèng)了一批與英格蘭布萊克本隊(duì)設(shè)計(jì)相同的球衣,因此這批球衣也同步給到了當(dāng)年成立的馬德里競(jìng)技,這也是馬競(jìng)最初和畢爾巴鄂一樣都穿藍(lán)白球衣的原因。

而最終一起換成紅白球衣的原因也很簡單:當(dāng)時(shí),畢爾巴鄂競(jìng)技董事會(huì)要求馬競(jìng)的一位即將去英國度圣誕假的董事,返回西班牙時(shí)給兩隊(duì)再帶一些藍(lán)白球衣。但這位董事把這項(xiàng)簡單的任務(wù)拖到了最后一天,卻發(fā)現(xiàn)已經(jīng)買不到了。
由于這位董事是要從南安普頓坐輪渡回國,因此最終他選擇購買了50件當(dāng)?shù)厍蜿?duì)南安普頓穿的紅白球衣。

于是,從這天起,兩支競(jìng)技隊(duì)的主場(chǎng)球衣就從藍(lán)白色變成了紅白色。而關(guān)于馬競(jìng)的裝備,還有一則額外的傳說故事:馬競(jìng)之所以選擇穿藍(lán)色短褲而非畢爾巴鄂競(jìng)技那樣的黑色短褲,是因?yàn)槔^續(xù)穿著了布萊克本的球褲。
沒錯(cuò),這是一個(gè)極具草根色彩的故事。而對(duì)于馬競(jìng)來說,無論是作為“分部”的創(chuàng)始,還是球衣顏色的巨大變化,都洋溢著職業(yè)足球早期發(fā)展階段那種并不那么死板的愉快氣質(zhì)。

這種氣質(zhì)也深深刻在了包括球衣和隊(duì)名的一切球隊(duì)歷史中。馬競(jìng)的隊(duì)徽上沒有皇冠,隊(duì)名上沒有御賜的“皇家”,甚至連“競(jìng)技”這二字都做過調(diào)整:弗朗哥時(shí)期,有一道關(guān)于禁止球隊(duì)使用外來詞作為名字的禁令,因此馬競(jìng)從和畢爾巴鄂一樣的Athletic變成了Atlético。
皇馬和巴薩作為球隊(duì)都有著比較明確的單一政治標(biāo)簽,但馬競(jìng)不同。就像這些故事透露出的氣質(zhì)一樣,馬競(jìng)的“不同”,似乎正在于這種“擁抱不同”的精神。而由這一系列有關(guān)球隊(duì)的歷史故事一起書寫出的集體記憶,塑造了在馬德里、西班牙甚至是歐洲足壇上的這種“平民”與“叛逆”的形象。
就像2017年那次馬德里德比時(shí),馬競(jìng)打出的TIFO一樣:Orgullosos de no ser cómo vosotros——Proud not to be like you,很自豪與你們不同。

這或許也是俱樂部在這樣一個(gè)環(huán)境里,書寫自己歷史故事的一個(gè)最重要的起點(diǎn)。
這樣的故事書寫也展現(xiàn)在了大都會(huì)球場(chǎng)的博物館里。
我曾去過一些球隊(duì)的stadium tour,此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札幌小巨蛋。那座球場(chǎng)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硬件:這是一座建在極寒之地的多功能可變形室內(nèi)球場(chǎng)。
然而大都會(huì)的體驗(yàn)是不同的,這座球場(chǎng)很新,很現(xiàn)代,很寬敞,但球隊(duì)的硬件與一眾現(xiàn)代化的新建球場(chǎng)比起來并沒有太多不同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,是球隊(duì)從博物館一進(jìn)門就開始講述的故事,以及傳達(dá)的態(tài)度。

馬競(jìng)的球場(chǎng)博物館里,最先能看到的是有關(guān)傳承的故事。無論是百年歷史的老球票、老證件,還是一代代父母子女流傳下來的老物件,都是作為珍貴文物放在玻璃柜中展出的內(nèi)容。在球隊(duì)歷史的部分,最先展示的也同樣是那些能讓我們感受到人的氣息的東西:球衣、球鞋,甚至是報(bào)紙頭版和參賽證件。

博物館的其他部分也是一樣。全世界的馬競(jìng)球迷通過這樣一支球隊(duì)聯(lián)結(jié)在一起,也自然不僅是靠“抗?fàn)幘瘛焙退^的“工人階級(jí)氣質(zhì)”。關(guān)于托雷斯的那段短片讓我印象深刻——影片的落腳點(diǎn)并不在球星的傳奇本身,而在于他的成長與傳承故事。這樣的講述方式將文化和競(jìng)技融合到了一起,才能感受到這支球隊(duì)的“競(jìng)技之道”。

故事也不止于此,在博物館里還有一些我在來到這里之前一無所知的故事。比如,馬競(jìng)的女子曲棍球隊(duì)。
馬競(jìng)一直是一家多項(xiàng)目的體育俱樂部,但女子曲棍球這個(gè)項(xiàng)目在公開的女性集體體育仍屬新生事物的20世紀(jì)30年代,依舊是一項(xiàng)創(chuàng)舉。很多人很難想象,當(dāng)馬競(jìng)的工人階級(jí)氣質(zhì)讓人覺得他們資源匱乏、缺少精英的情況下,是如何在那個(gè)年代孕育出了如此先鋒的隊(duì)伍。

與一些大俱樂部直到近十年來才姍姍來遲地成立女足部門,將女子足球作為純粹的點(diǎn)綴不同,馬競(jìng)的這種探索和嘗試是令人驚嘆的。這支女子曲棍球隊(duì)在當(dāng)時(shí)就有固定的訓(xùn)練與參賽體系,且在競(jìng)技水平上能夠連續(xù)奪冠,并為國家隊(duì)輸送了大量運(yùn)動(dòng)員,證明了馬競(jìng)作為俱樂部的投入并非花拳繡腿。

馬競(jìng)的工人階級(jí)氣質(zhì)和這樣一支大部分球員都來自新式教育學(xué)校的女子隊(duì)伍看起來背離,但實(shí)際上只是兩條并行的路線罷了。正是球隊(duì)的競(jìng)技屬性才決定了這支球隊(duì)成為了當(dāng)時(shí)女子集體球類運(yùn)動(dòng)進(jìn)入大眾視野的先驅(qū)之一,也證明了職業(yè)俱樂部最初的組織形式在所有性別、所用項(xiàng)目上的普適性。
這也是馬競(jìng)博物館敘事的共同主線:這是一家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傳承的球隊(duì),一家從父到子一代代延續(xù)的球隊(duì),而不僅是用單一的“平民”或者“抗?fàn)帯本湍芏x的球隊(duì)。
就像讓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幕,一部講述馬競(jìng)歷史和文化、幾乎只字未提競(jìng)技成績的小短片結(jié)束后,漆黑的放映室里沒有開燈,唯一的光線來自屏幕升起后看到的屏幕后的房間。

那是榮譽(yù)室,里面放滿了一排又一排西甲和國王杯的獎(jiǎng)杯。
放眼西班牙足壇,馬競(jìng)并不是一家只講文化不談競(jìng)技的俱樂部。只是在展示那并不算少的獎(jiǎng)杯前,馬競(jìng)還有更重要的故事想講。
最后的一部分是必須要看的一場(chǎng)比賽。
由于我安排的行程在男足的國際比賽日期間,卻正是在女足的國際比賽日前,所以我能剛好趕上一場(chǎng)馬競(jìng)與曼聯(lián)的歐冠比賽。

比賽的場(chǎng)地不在大都會(huì),而是在大約30分鐘車程的近郊。那是一座小鎮(zhèn)里的小球場(chǎng),小鎮(zhèn)叫Alcalá de Henares,埃納雷斯河上的城堡,是塞萬提斯的故鄉(xiāng),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的世界遺產(chǎn)。
小球場(chǎng)是在這個(gè)足球高度商業(yè)化的時(shí)代拉近球迷和球隊(duì)距離的最好媒介。球場(chǎng)雖小卻五臟俱全,賽前的官方商店里人滿為患,男女兩款球衣琳瑯滿目。

我坐在了長邊看臺(tái)的下層第二排,對(duì)角線位置是客隊(duì)球迷,而其他座位都被主隊(duì)球迷填滿了。身邊有很多異常熱情的馬競(jìng)球迷,穿著今年、去年或者是10年前、15年前的馬競(jìng)球衣。
最后,馬競(jìng)很遺憾地輸?shù)袅诉@場(chǎng)歐冠聯(lián)賽階段的卡位戰(zhàn)。球隊(duì)長時(shí)間多打一人,進(jìn)攻卻一直無功而返。球場(chǎng)的東西沒那么好吃,馬德里10月的夜晚也有些涼意。但球迷實(shí)在是太熱情了,而且這種熱情隔著幾乎是零距離能與場(chǎng)上的球員產(chǎn)生互動(dòng)。
看臺(tái)每一層的最后一排是無障礙座位。那一天,這排無障礙座位上停滿了輪椅,輪椅上掛滿了俱樂部色彩的球迷裝備。
??在各個(gè)平臺(tái)關(guān)注我們,獲得持續(xù)更新。??


在這次去馬德里之前,我先經(jīng)過了巴黎和巴塞羅那。
在巴黎街頭的幾乎每一處游客商店里,都擺著至少一個(gè)柜子的巴黎圣日耳曼周邊,甚至有不少店鋪的遮雨棚上都有兩個(gè)大大的PSG隊(duì)徽;而在巴塞羅那,機(jī)場(chǎng)落地的第一時(shí)間就能在航站樓里看到巴薩的官方商店,大街小巷和每一處知名地標(biāo)你都能看到很多件亞馬爾球衣。
這兩座城市在足球上有一些共同特點(diǎn):在巴塞羅那幾乎看不到任何西班牙人俱樂部的元素,在巴黎也完全沒有巴黎FC。贏家通吃,這對(duì)于很多擁有壓倒性榮譽(yù)優(yōu)勢(shì)豪門的城市來說,似乎是足球市場(chǎng)的一般規(guī)律。

但馬德里有所不同。
從某個(gè)角度來說,皇馬在世界足球史上的地位更甚,也有著更加深厚的“官方”背景,甚至曾一度被國家機(jī)器作為標(biāo)志球隊(duì)用于足球的宣傳敘事。
這光是從主場(chǎng)的位置就能看出不同:伯納烏的位置在馬德里的富人區(qū)查馬丁區(qū),甚至當(dāng)?shù)厝藭?huì)將這片馬德里房價(jià)最貴的商業(yè)區(qū)稱呼為“伯納烏區(qū)”。而馬競(jìng)的老主場(chǎng)卡爾德隆球場(chǎng)則是在西南的曼薩納雷斯河邊,著名的看臺(tái)下穿M30公路奇景,也正是這座球場(chǎng)所處位置的證明。甚至,馬競(jìng)的新主場(chǎng)大都會(huì)球場(chǎng)位于更遠(yuǎn)的馬德里東郊,從市區(qū)駕車過去還要經(jīng)過一段高速公路。

然而,在馬德里的足球版圖上,皇馬從未獨(dú)占鰲頭。馬競(jìng)憑借著自己獨(dú)特的魅力,始終占據(jù)著很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這與倫敦、米蘭和伊斯坦布爾的情況又有一些不同:阿森納和切爾西在國內(nèi)和洲際賽事中各擅勝場(chǎng),米蘭兩隊(duì)的頂級(jí)聯(lián)賽冠軍次數(shù)僅差1次,伊斯坦布爾則是三支球隊(duì)分庭抗禮壟斷國內(nèi)聯(lián)賽。而馬競(jìng)和皇馬相比,在頂級(jí)聯(lián)賽的奪冠次數(shù)上相差三倍之多,洲際賽事榮譽(yù)方面皇馬更是處于絕對(duì)領(lǐng)先地位。
但馬競(jìng)依舊能做到。

當(dāng)我深夜穿著馬競(jìng)球衣走在馬德里街上或是坐上出租車的時(shí)候,騎著車的年輕人和年長的出租車司機(jī)依舊會(huì)朝我喊Aúpa Atleti。這是馬競(jìng)的生存之道,也是馬德里的競(jìng)技之道。
馬競(jìng)的起源故事就很特別。
在20世紀(jì)初,現(xiàn)代足球剛剛開始從不列顛走向世界的過程中,馬競(jìng)的起源要通過二度關(guān)系才與英國產(chǎn)生了聯(lián)結(jié):來自巴斯克的留英學(xué)生返回西班牙后成立了畢爾巴鄂競(jìng)技俱樂部,而三名住在馬德里的巴斯克學(xué)生則成立了競(jìng)技的馬德里分部,也就是最初的馬德里競(jìng)技。
這一份聯(lián)結(jié)甚至也體現(xiàn)在了球衣上:1903年,愛爾蘭裔的畢爾巴鄂競(jìng)技俱樂部成員胡安·莫澤給俱樂部捐贈(zèng)了一批與英格蘭布萊克本隊(duì)設(shè)計(jì)相同的球衣,因此這批球衣也同步給到了當(dāng)年成立的馬德里競(jìng)技,這也是馬競(jìng)最初和畢爾巴鄂一樣都穿藍(lán)白球衣的原因。

而最終一起換成紅白球衣的原因也很簡單:當(dāng)時(shí),畢爾巴鄂競(jìng)技董事會(huì)要求馬競(jìng)的一位即將去英國度圣誕假的董事,返回西班牙時(shí)給兩隊(duì)再帶一些藍(lán)白球衣。但這位董事把這項(xiàng)簡單的任務(wù)拖到了最后一天,卻發(fā)現(xiàn)已經(jīng)買不到了。
由于這位董事是要從南安普頓坐輪渡回國,因此最終他選擇購買了50件當(dāng)?shù)厍蜿?duì)南安普頓穿的紅白球衣。

于是,從這天起,兩支競(jìng)技隊(duì)的主場(chǎng)球衣就從藍(lán)白色變成了紅白色。而關(guān)于馬競(jìng)的裝備,還有一則額外的傳說故事:馬競(jìng)之所以選擇穿藍(lán)色短褲而非畢爾巴鄂競(jìng)技那樣的黑色短褲,是因?yàn)槔^續(xù)穿著了布萊克本的球褲。
沒錯(cuò),這是一個(gè)極具草根色彩的故事。而對(duì)于馬競(jìng)來說,無論是作為“分部”的創(chuàng)始,還是球衣顏色的巨大變化,都洋溢著職業(yè)足球早期發(fā)展階段那種并不那么死板的愉快氣質(zhì)。

這種氣質(zhì)也深深刻在了包括球衣和隊(duì)名的一切球隊(duì)歷史中。馬競(jìng)的隊(duì)徽上沒有皇冠,隊(duì)名上沒有御賜的“皇家”,甚至連“競(jìng)技”這二字都做過調(diào)整:弗朗哥時(shí)期,有一道關(guān)于禁止球隊(duì)使用外來詞作為名字的禁令,因此馬競(jìng)從和畢爾巴鄂一樣的Athletic變成了Atlético。
皇馬和巴薩作為球隊(duì)都有著比較明確的單一政治標(biāo)簽,但馬競(jìng)不同。就像這些故事透露出的氣質(zhì)一樣,馬競(jìng)的“不同”,似乎正在于這種“擁抱不同”的精神。而由這一系列有關(guān)球隊(duì)的歷史故事一起書寫出的集體記憶,塑造了在馬德里、西班牙甚至是歐洲足壇上的這種“平民”與“叛逆”的形象。
就像2017年那次馬德里德比時(shí),馬競(jìng)打出的TIFO一樣:Orgullosos de no ser cómo vosotros——Proud not to be like you,很自豪與你們不同。

這或許也是俱樂部在這樣一個(gè)環(huán)境里,書寫自己歷史故事的一個(gè)最重要的起點(diǎn)。
這樣的故事書寫也展現(xiàn)在了大都會(huì)球場(chǎng)的博物館里。
我曾去過一些球隊(duì)的stadium tour,此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札幌小巨蛋。那座球場(chǎng)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硬件:這是一座建在極寒之地的多功能可變形室內(nèi)球場(chǎng)。
然而大都會(huì)的體驗(yàn)是不同的,這座球場(chǎng)很新,很現(xiàn)代,很寬敞,但球隊(duì)的硬件與一眾現(xiàn)代化的新建球場(chǎng)比起來并沒有太多不同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,是球隊(duì)從博物館一進(jìn)門就開始講述的故事,以及傳達(dá)的態(tài)度。

馬競(jìng)的球場(chǎng)博物館里,最先能看到的是有關(guān)傳承的故事。無論是百年歷史的老球票、老證件,還是一代代父母子女流傳下來的老物件,都是作為珍貴文物放在玻璃柜中展出的內(nèi)容。在球隊(duì)歷史的部分,最先展示的也同樣是那些能讓我們感受到人的氣息的東西:球衣、球鞋,甚至是報(bào)紙頭版和參賽證件。

博物館的其他部分也是一樣。全世界的馬競(jìng)球迷通過這樣一支球隊(duì)聯(lián)結(jié)在一起,也自然不僅是靠“抗?fàn)幘瘛焙退^的“工人階級(jí)氣質(zhì)”。關(guān)于托雷斯的那段短片讓我印象深刻——影片的落腳點(diǎn)并不在球星的傳奇本身,而在于他的成長與傳承故事。這樣的講述方式將文化和競(jìng)技融合到了一起,才能感受到這支球隊(duì)的“競(jìng)技之道”。

故事也不止于此,在博物館里還有一些我在來到這里之前一無所知的故事。比如,馬競(jìng)的女子曲棍球隊(duì)。
馬競(jìng)一直是一家多項(xiàng)目的體育俱樂部,但女子曲棍球這個(gè)項(xiàng)目在公開的女性集體體育仍屬新生事物的20世紀(jì)30年代,依舊是一項(xiàng)創(chuàng)舉。很多人很難想象,當(dāng)馬競(jìng)的工人階級(jí)氣質(zhì)讓人覺得他們資源匱乏、缺少精英的情況下,是如何在那個(gè)年代孕育出了如此先鋒的隊(duì)伍。

與一些大俱樂部直到近十年來才姍姍來遲地成立女足部門,將女子足球作為純粹的點(diǎn)綴不同,馬競(jìng)的這種探索和嘗試是令人驚嘆的。這支女子曲棍球隊(duì)在當(dāng)時(shí)就有固定的訓(xùn)練與參賽體系,且在競(jìng)技水平上能夠連續(xù)奪冠,并為國家隊(duì)輸送了大量運(yùn)動(dòng)員,證明了馬競(jìng)作為俱樂部的投入并非花拳繡腿。

馬競(jìng)的工人階級(jí)氣質(zhì)和這樣一支大部分球員都來自新式教育學(xué)校的女子隊(duì)伍看起來背離,但實(shí)際上只是兩條并行的路線罷了。正是球隊(duì)的競(jìng)技屬性才決定了這支球隊(duì)成為了當(dāng)時(shí)女子集體球類運(yùn)動(dòng)進(jìn)入大眾視野的先驅(qū)之一,也證明了職業(yè)俱樂部最初的組織形式在所有性別、所用項(xiàng)目上的普適性。
這也是馬競(jìng)博物館敘事的共同主線:這是一家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傳承的球隊(duì),一家從父到子一代代延續(xù)的球隊(duì),而不僅是用單一的“平民”或者“抗?fàn)帯本湍芏x的球隊(duì)。
就像讓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幕,一部講述馬競(jìng)歷史和文化、幾乎只字未提競(jìng)技成績的小短片結(jié)束后,漆黑的放映室里沒有開燈,唯一的光線來自屏幕升起后看到的屏幕后的房間。

那是榮譽(yù)室,里面放滿了一排又一排西甲和國王杯的獎(jiǎng)杯。
放眼西班牙足壇,馬競(jìng)并不是一家只講文化不談競(jìng)技的俱樂部。只是在展示那并不算少的獎(jiǎng)杯前,馬競(jìng)還有更重要的故事想講。
最后的一部分是必須要看的一場(chǎng)比賽。
由于我安排的行程在男足的國際比賽日期間,卻正是在女足的國際比賽日前,所以我能剛好趕上一場(chǎng)馬競(jìng)與曼聯(lián)的歐冠比賽。

比賽的場(chǎng)地不在大都會(huì),而是在大約30分鐘車程的近郊。那是一座小鎮(zhèn)里的小球場(chǎng),小鎮(zhèn)叫Alcalá de Henares,埃納雷斯河上的城堡,是塞萬提斯的故鄉(xiāng),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的世界遺產(chǎn)。
小球場(chǎng)是在這個(gè)足球高度商業(yè)化的時(shí)代拉近球迷和球隊(duì)距離的最好媒介。球場(chǎng)雖小卻五臟俱全,賽前的官方商店里人滿為患,男女兩款球衣琳瑯滿目。

我坐在了長邊看臺(tái)的下層第二排,對(duì)角線位置是客隊(duì)球迷,而其他座位都被主隊(duì)球迷填滿了。身邊有很多異常熱情的馬競(jìng)球迷,穿著今年、去年或者是10年前、15年前的馬競(jìng)球衣。
最后,馬競(jìng)很遺憾地輸?shù)袅诉@場(chǎng)歐冠聯(lián)賽階段的卡位戰(zhàn)。球隊(duì)長時(shí)間多打一人,進(jìn)攻卻一直無功而返。球場(chǎng)的東西沒那么好吃,馬德里10月的夜晚也有些涼意。但球迷實(shí)在是太熱情了,而且這種熱情隔著幾乎是零距離能與場(chǎng)上的球員產(chǎn)生互動(dòng)。
看臺(tái)每一層的最后一排是無障礙座位。那一天,這排無障礙座位上停滿了輪椅,輪椅上掛滿了俱樂部色彩的球迷裝備。
??在各個(gè)平臺(tái)關(guān)注我們,獲得持續(xù)更新。?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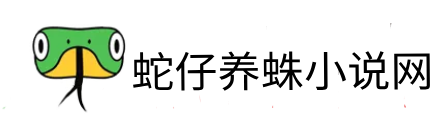

章節(jié)評(píng)論
段評(píng)